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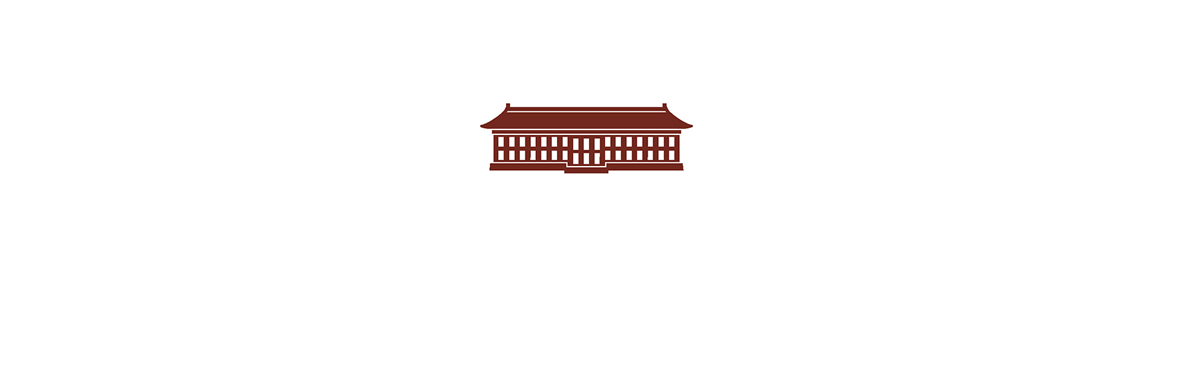



专业选择

Q:学长决定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是很早就想好了?
A:我本科是PPE专业(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高三的时候虽然对大学专业不甚了解,但觉得政治、经济和哲学这些学科都很有意思,希望能都有所涉猎。高考我很幸运地进了元培学院,一入学就选择了高中时向往的PPE专业。大一时候我因为数学不好,觉得经济学对我来说难如登天,也发觉政治学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有趣,却在哲学的入门课中得到了许多“正反馈”。于是,我在大一结束时打定了学习哲学的念头。
我是在大二决定尝试以马哲作为方向。大二下学期的时候疫情在家,有些无所事事,但其实心中也很忧虑,思考将来要选择什么具体的专业方向,要做什么。当时恰好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虽然是我们的专业课,但这门课上的阅读让我感到最有兴趣,也更能读懂,同时也很现实地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较好的前景不至于未来陷入尴尬的境地。因此我初步决定学习马哲,给我现在的导师试探着发了邮件请教,开始尝试进入马哲学科,一步一步走下来,相对顺利地走到了今天。
我之前总是半开玩笑地说,我读马克思的文本最有亲切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出身自一个“工农阶级”的家庭,马克思的文本所描述的事情更加契合我过去的见闻和生活体验,对我的生活更有解释力。我从字里行间能够读出我遇到的问题,或者我隐约的想法。就像看到电影情节联想到自己的生活一样,马克思的作品也能让我有这种感觉,我也由此受到鼓舞,越读越多。

缪辰生活照

课余生活

Q:学长疫情在家的学期除了确立了学术兴趣,还有其他有趣的经历吗?
A:20年那时我穷极无聊,写作了许多“不上台面”的随笔,讲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或者套作一些耳熟能详的诗词。我的这些小故事受到之前阅读过的一些作家的影响:卡尔维诺,博尔赫斯,还有菲利普·迪克,他们写的一些奇幻故事对我影响很大,让我也写了一些校园风格的奇幻故事。有的作品发在“全元光滑”上,比如这篇《纯属虚构》。

点击图片阅读全元光滑推送缪辰作品《纯属虚构》
Q:学长和全元光滑的主创们是怎么认识的,有没有比较有趣的故事?
A:不仅是全元光滑,其他最好的朋友们也都是从军训开始认识的,军训时候的舍友,现在大多都是很好的朋友。在智慧书院上还能找到一个叫“三道口研究院”的组织,其实是我们几位朋友聚在一起,随便聊聊生活和学业的事情。大家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视角出发聊一些热点事件,比如之前引发热议的外卖骑手与大数据系统,以及自己学业上的构想等等。
我觉得这也是元培的好处,不仅是我可以教他们学《理想国》,他们可以教我计算概论,更是在于学科跨度很大的同学们有机会相互接触,成为很好的朋友。

“三道口”同学们与元培教师合影
Q:学长是怎么加入地下电影院的呢?
A:2018年我还没入学,在新生群里看到一位学长的群名片写着“欢迎加入元培地下电影院”,我因为对电影的兴趣,就自荐加入他们。在当时地下电影院的主要成员——15、16级的同学——进行线上面试之后,我就在没有见面的情况下加入了地下电影院。
我中学时很爱看电影,从13岁开始,初中三年看了300多部电影,也是那时开始用豆瓣,看一部做一部的标记。大学凭借以前的兴趣加入了地院。之后决定在地院继续发展,是觉得这里的朋友也能够作为生活中的同伴互相交流。至少从我进入地院以来,我们一直不太以阅片量来作为评判标准,大家更看重的并不是鉴赏电影的能力,而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理解、成为好朋友的氛围。
Q: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地院成员可以向我们介绍一下?
A:我一开始认识的朋友都是比我年纪大一些的同学,15级的楚显琨、16级的何杨是地院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掌门”,在我融入大学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多帮助,也让我在地院找到一个生活的锚点。当时地下室还没装修,学长学姐经常会带我们一起在地院聚餐,冬至吃饺子等等。我在那里认识了大学最初的许多好友,比如现在已经毕业去清华读研究生的伍修毅。
19年时,地院创始人楚显琨毕业了,我更加深入地参与到了地院的管理工作中;19到21年不断招入新同学,继续融入集体。我觉得地院的氛围很好的一点,就是大家不会太在意年级,我跟比我大三四岁的学长学姐们都没有包袱地相处,和年级更低的同学们也玩得很开心。在地院认识的几位19级同学也都在我困难时给了我很多帮助。

元培地下电影院同学合影
大家参与地院的活动很少是为了直接功利的目的,这个并非官方的组织对升学或填写简历几乎没有任何帮助,只是让我们通过电影这种载体获得一些确定感和充实感。愿意融入其中的同学大概也是希望在各种奔波忙碌之外寻找一块暂时休息的地方。不过这两年,年纪更小的同学们似乎越来越缺少这种时间或动力,寻求一个暂时逃避繁杂的地方的需求可能也越来越弱,大抵是时代氛围如此。
Q:地院是一个类似社团性质的组织吗?
A:是的,一开始是想作为书院内部的社团来做,但实际更像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玩,不过随着这些关系密切的老朋友们纷纷毕业,新的同学们有新的办法,地院将来也许会成为有更规范运作流程的书院俱乐部,可能没有建立初期那样轻松但也会以新的更有组织化的形态为书院提供公共服务。
在17年地院初创时,创始的成员们买了很多旧电影杂志,撕掉贴在墙上,费了很多心力把这里打造成自己的“据点”。吴艳红老师以前还跟我说,“感觉你在那里就像回到家一样”。我也很希望之后的同学们能够有热情去做这些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事,把这个空间当成能够暂时逃避外部世界的纷扰的地方,虽然这并不容易。
Q:除了日常放映以外,地院还有其他流程规范化的活动吗?
A:我们每年都会拍剧照,是从17年开始的老传统。陈子维很会摄影,最初他会带着地院的朋友们一起模仿电影剧照里的经典场景。我们19年去俄文楼的阁楼翻拍《落水狗》的枪战片剧照,赵橙阳和陈子维几个人穿着西服、拿着道具“手枪”,正在阁楼热闹地摆出造型的时候,李猛老师带着来访的客人往楼上走,我们迅速藏到屏风后面,手里拿着道具向外张望。这些有意思的时刻也成为了朋友们的难忘回忆。

《落水狗》剧照翻拍
剧照的海报是同学们自己选的,因为我一直觉得地下电影院不是要求别人做事的学生组织。选片也不是让某个人安排片单,强制要求某个固定的时间放某部电影,而是大家自由填写。但这种模式近两年也有点小尴尬,同学们现在没有频繁放电影的动力,组织过程也会遇到一点麻烦。如果没办法从这件事本身中获得成就感,而只是把它看作任务,就会感到艰难。选择自己想放映的电影,把喜欢的电影推荐给别人,本身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每年也会有固定放映的电影,4月初的时候会放张国荣,12月底临近跨年的时候会放映《真爱至上》。地院放映的另一个传统是每部电影都会建一个交流群,一部叫《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动画在地院放了三次,一直都用同一个群聊,大家平常会转发各种相关内容,随便聊聊天。这也是我希望看到的——虽然是很偶尔的事情——有一些没那么紧密的、大家能随便聊天的地方。
Q:地院有没有对电影风格类型的整体偏好?
A:有一次我们请陈斯一老师来做沙龙讲座,他打算选择《银翼杀手》,我问老师为什么选这部,陈老师说他看了我们的片单,感觉这个比较符合我们的风格和爱好。但其实我们没有非常固定的风格。18年的时候,地下电影院曾经在树洞上被吐槽“选的片都很俗,没有地下的感觉”。他们大概不知道“地下”只是因为我们确实在地下,而不是因为选片有某些“地下感”的特征。

陈斯一老师在地院做电影讲座
我们虽然有时候会放冷门电影,但大多数都是相对耳熟能详、有较广泛受众的电影,因为我们希望地院是一个面向全院乃至全校同学的场所,一个大家都能找到爱好的场所,而不是一个自娱自乐的封闭小团体。
我们也会做一些电影沙龙,请各学科的老师和同学一起看电影,分享观影的感受,到现在已经办了近三十场。老师们都有自己的电影偏好,会讲自己对电影和自己的学科的看法。最初是楚显琨给老师们分别发邮件邀请,他当时还邀请了戴锦华老师,但没能如愿。元培书房和我们去年请戴老师做讲座,讲法国电影《悲惨世界》的时候,我自我介绍说我是地下电影院的负责人,戴老师说她还记得三年前我给她发的邮件——老师不知道地院那时的负责人并不是我。
Q:地院院衫上面写的那句话“海拔约等于未名湖底”,是谁提出的?
A:它17年就已经存在了,我也不知道地院的创始人们最初的创想何来。不过据说这里的海拔确实约等于未名湖底。

阅读和观影

Q:学长说过自己在上大学之前对电影的兴趣成为了你加入地院的契机,对一些作家的兴趣影响了你写作的风格。可以谈谈这样的兴趣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吗?
A:从12岁开始我逐渐懂事,偶然读到雨果的《悲惨世界》。这对我在道德教化上有一种启蒙的意义,并且它无论是波澜壮阔的故事还是文笔都吸引了我,至今仍然是我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我在豆瓣上标的第一部电影是悲惨世界的音乐剧。在那之后,我开始对自己的成长有比较系统的梳理。随后又读到一些18、19世纪的文学著作,再之后我发现了卡尔维诺等作家,开始更加喜欢这些新奇的事情,而没有机会再沉下心来去读鸿篇巨制了。《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这类应该一读的书,都一直摆在我的书架上,没再读完过。之前上孙飞宇老师的课,他跟我们说“有些书现在不读,以后就再也没机会读了”,现在想来确实如此。

《悲惨世界》十周年纪念演唱会
我在十四五岁的时候读到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非常震惊:原来小说还能这么写。最开始读的博尔赫斯作品是《交叉小径的花园》,后来读到《沙之书》等等。他的故事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创意,比如“遇见另一个世界的自己”,很多后来被各种电影不断翻拍的母题也都在他的小说中有最初的体现。这些奇特的创想吸引我在十四五岁读了不少以这两位为代表的一些作品。虽然我现在很少读文学作品,但因为小时候读到了这些作家,相当程度上塑造了我现在的喜好。
我当时还读到一些“偏门”作品,比如波兰作家布鲁诺·舒尔茨的小说集《鳄鱼街》,这些奇奇怪怪的创想给了当时的我强烈的震撼,以至于我写作文都想模仿那种怪异冷漠又带一点奇异的温情的笔调。我始终没有办法成功模仿那几位作家的风格,班门弄斧的结果就是我那些奇奇怪怪的小故事。这些奇特的构想给了当时和现在的我很多启发,可能现在我想不起来他们具体的完整的故事,但他们给我的整体印象成为了我写作、谈话、思想背景的一部分。
那时是我的最初探索,也是世界观的初步形成。我那时也会有意识地去读耳熟能详的作家作品,强迫自己读非常艰涩的《尤利西斯》。虽然读不懂《尤利西斯》,但我很喜欢乔伊斯的《都柏林人》那部短篇小说集,最后一篇描述一场雪景,至今每当下雪的时候我都会想到那个场景。我那时也很喜欢聂鲁达的情诗和自传,现在则更能欣赏他中晚期的那些作品,比如《马丘比丘之巅》。我当时的阅读更多是出于兴趣去读小说和诗歌,看起来似乎只是为了开心的事情,却对我的人生观形成却起到了很大影响,给了我基本的文学素养和道德启蒙。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也许会得到一些意外收获,看电影也是这样。
Q:好像看书跟看电影这两段经历都是同一时间开始的?
A:看书和看电影都让那时的我了解到世界上不同时代、不同地方的人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我们现在的生活有怎样的可能性。从他们的处境中,我们也能反思自己的生活。
我当时最喜欢的那些电影中有一类是《机遇之歌》、《无姓之人》、《罗拉快跑》等等,这些电影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主角去做一件事情不太成功,感到懊悔,时间就回退到了他做出选择之前,让他选择去经历另外一番命运。我刚进入大学时乃至大学期间,各种可能性在我面前展开,这些电影给了我一些最初的教益和想象,启发我如何看待我所面临的生活和未来的可能性。
它们不单是讲关于可能性的故事,也包含导演在不断重复中想表达的主旨。比如《机遇之歌》,三次赶火车引发三种不同的命运,导演想讲的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不是时间几分几秒的差距会带来的机缘巧合,而是小人物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必然卷入洪流,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非常关注的话题。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话语中,这大概会被表述为个人能动性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渺小的、看似无力的个人,在一个异己的、可能会让愿望落空、支配我们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的社会结构面前,在看似庞然大物,无法具体指出“他是谁”的社会力量面前,我们能做到什么,能期望什么?我觉得无论在学业还是个人的生活现状中,这都是我们时时刻刻需要应对的极具普遍性的问题。

《机遇之歌》追逐火车的经典场景
还有一位电影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他是一个意大利共产党。大家都知道他拍过《末代皇帝》,还拍过令人惊讶的《戏梦巴黎》,但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同流者》,是一部能够让人时时刻刻反思某种思想倾向的、有启发意义的作品。
我最喜欢的几部电影,首先是《银翼杀手》,之后是《机遇之歌》、《同流者》、《悲惨世界》音乐剧、《追捕聂鲁达》、《砂制时镜下的疗养院》等等。大多数都是我在大学之前看的电影,但大学之后我又许多次重看它们。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在我的理解里表达的是对于自我内心最深处渴望的探寻。它讲的是三个探险家想要进入一个神秘的房间,那个房间据说能实现人心最深处的愿望,把它们以物质形态呈现在你面前。“探索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是我在学习和生活中会去关注的问题。当代对流行文化的许多解读会说:你所想要的只是大众媒体灌输给你的,只是当下的资本体制在操控你的渴望。这样的传播学以及激进哲学理论,现在普遍被人们用来解读流行的短视频平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你真正想要实现的渴望是什么?是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吗?甚至,真的有这样本应实现的理想状态吗?如果有,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到它,或者说,是否能有一种不被社会结构和资本所控制的个人意识形态?如何对自己、对自己的处境、对未来的希望有所意识?我觉得电影关注的这些问题也是现实中人们会遇到的问题,这不仅是所谓现代性造成的问题。这也让我反思自己的生活:对于我来说,我所渴望之物是真正重要的吗?他们因何重要?
前几个月很火的一部名叫《赛博朋克·边缘行者》的电影,也在前现代的意义上表达了这个问题:我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在亲人朋友的各种压力中,以及社会期待的种种压力中,究竟为何而活,是为别人而活,还是为自己而活?就像吃薯条的海鸥漫画里的那个问题:“我们将飞向何方?”即使不考虑那些花哨的理论,不谈论大众传媒的虚假控制,在这些现代问题的层面之外,回到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层面,这些宏大又切身的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
此外还有一类作品,我把它们归到一起:一部名叫《巴比伦柏林》的电视剧,一部名叫《极乐迪斯科》的游戏,一部去年上映的名叫《法比安》的德国电影,等等。从表面剧情上来看,它们都只是警探破案之类的线索较弱、刺激性并不强的故事,但我觉得它们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感受: 面临时代变局的小人物,受到过去历史的纠缠,也被笼罩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紧张事件的阴影中,他在街道上奔走探险,在数股力量之间周旋,看到每个人的阴影,又被所有阴影笼罩。这些作品的巧妙之处在于,简单的故事完成的时候,整个世界或者整个能够感受到的生活中的一切危机恰恰是悬而未发的。他感觉到他生活中的这些短暂的希望和平静都随时可能破灭,在自己的内心之中应当选择何种价值观,自己的道路应该走向何方,以及外在世界的矛盾冲突将会走向何方,都处于不确定的阴影之中,但是这些主角仍然需要坚定地投身于不确定的未来。有人选择享受当下的歌舞繁华,但不确定的未来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我在19、20、21年分别看到这些作品,都很有感触,可能也是因为感受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迅速的改变,过去和现在的生活可能只是转瞬即逝的幻象。我们将会选择什么信条去应对不确定性,在动荡的生活中怎么安顿自己,也是这些电影给我的一些与现实相结合的感触。

游戏《极乐迪斯科》的插图
这个问题在切身生活中往往不以那么严峻的形式表现在我们面前。大二的时候,我最先感受到的迷茫是将来在本科结束后走向何方,选择何种职业道路。这种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感受,我觉得是每个人在当今时代都能时刻感受到的。我想我可以像《极乐迪斯科》的那位主角一样,可以在一次次与人交谈中获得属于自己的信念。
对我未来选择什么职业问题的解答,也恰好成为了对不确定的时代的回答。我当时因为课程原因读到了马克思,也开始去真正学习他,开始以马克思的视野作为望远镜和放大镜来观察我的生活,通过阅读来串联起自己曾经从书和电影中看到的别人的生活状态,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在这种现在可能还很脆弱的认识中,投身于不确定的未来,这是我喜欢这类作品的原因。《法比安》也是讲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作品,讲的是一个失业的德国博士在街头无所事事时的奇遇,我们将来会不会也这样呢(笑)。
刚才说的这些也算是我的成长经历,我的阅读、我的学习、我看的这些电影,最终落到了对自己生活的认识。

学术与生活

Q:学长在学术上的兴趣似乎跟平时阅读和观影的兴趣是相连的?
A: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大程度上会将它当成一份事业。学习中偶尔读到或者必须要读的东西可能会影响我的信念、对各种事情的认识,我不可避免地会在生活中依照这些准则或价值判断做事情,但我还是会希望把事业和日常生活区分开来。
我本科生科研研究的是一位激进“疯狂的”左派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鲍德里亚,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这个词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他以一种非常激进和叛逆的态度批判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又有一种绝望的色彩,认为人们很难从固有的社会结构中挣脱出来,从社会结构中尝试挣脱的努力其实都是社会结构预定好的——他的著作经常以忧伤的笔调表达这样的观点。我们熟悉的那些“近未来”的科幻作品,比如《银翼杀手》,讲述的故事也是一些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但社会又以他们为基础的“无产阶级”边缘人,试图反抗不合理的资本主义体制,但这些反抗又恰恰是被体制所预料到并且被纳入其中的。这也是《黑客帝国》所表达的其中一层意思:你看似在反抗,但反抗其实是超级计算机系统matrix设计好的,它让你通过反抗得到一种满足的感觉,但其实你还是在控制之下。鲍德里亚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悲观延伸到他对个人在具体生活处境中的悲观,他认为个人很难从无处不在的资本主义拜物教漩涡之中挣脱出来。

激进的思想家鲍德里亚
如果我把事业和生活混为一体,那可能受到他的影响会采取一种消极灰暗的处事态度。但如果把它只当成一项事业、一个对象,就不会如此。一个评论家说:读鲍德里亚主要是为了好玩,我可以说也是如此。我可以在学术上评议他,分析他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可以看到他讨论的事情在我的生活中以怎样的面貌出场,但不会把他对这些事情的评议带入到具体的生活选择中。阅读他们的作品只是让我认识到生活中这些问题可能是确实存在的,但我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问题,并不需要受到某位作家或思想家的约束。
Q:学长的表达整体上非常流畅,感觉你从十二岁以来的记忆都有清晰的定位和规划,或者说你可能是一个经常回望自己的人。
A:确实经常回望。每一个和我聊到这里的人,我都会给他们展示一下我引以为豪的周记,我能查到自己过去几年来的某一天我在做什么事情。写周记最开始还是中学时候为了安排好时间,后来却形成了这么独特怪异的习惯,连中学时的同学们都会觉得诧异。
做这些(记周记)还是想对自己的生活有一种掌控感,能知道自己这一周或者这段时间做了什么。虽然这两周时间可能被我浪费了,但我知道我这两周是去玩游戏、去看电影了,哪怕是单纯的刷手机,知道把时间浪费在了何处,能看到虚掷时光所激起的水花。我不常有明确的短期计划,中期长期的计划也不甚明确,但这种对自己过去的回望,能够让我踏实地感觉到自己每天都在切实地生活。这也和我刚才说到的问题相关,面对宏大的外在世界,我们自己能做些什么,能实现什么、期望什么?我记录这些也是在对抗虚无感和无力感,是对自己诚实,让自己踏实。
Q:研究生会比本科生的时间要宽裕一些吗?压力变大还是变小了?
A:在课程上更时间宽裕,我这学期15学分,5门课,周一到周五每天上课三个小时,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但也能列出更多要做的事情:更多要读的书,要看的论文,要写的东西,要为将来更加正式的论文所做的准备。之前本科没学好的很多事情,到了研究生阶段发现自己还是要去补上。压力相比大四肯定是变大了。我在豆瓣开玩笑说:从大四到研究生就像是在中超踢了半年之后,被曼联签去踢欧联。研究生阶段会遇到什么,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不确定的,但这种不确定更像是玩游戏的时候地图一片黑暗,探索的时候反而会有种“有所期待”的感觉。

王稼军教授给缪辰颁发本科毕业证书

现在比我小几岁的同学们陷入了更大的选择的纠结,会很在意将来本科毕业怎么保研,出国政策会怎样。这些确实都是应该担心的,但是我觉得现在走出的每一步都不会是最终具有决定性的那一步,将来会发生什么还未可知。就像《巴比伦柏林》这部剧的主角,他在20年代无论选择哪种立场,都不会想到30年代世界的变化,更不会想到60年代,他的朋友成为了西德的第一任总理。这些更长时间尺度的跌宕起伏,都不会在一个普通人的眼中被看到。也许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这样,个人的认识能力有限,看似最重要的抉择最终可能都不是具有决定性的一步。这也只算是一种宽慰的想法吧,我们都知道事情没那么容易,人各有各的难处,没人有普遍性的解决方案。
之前我和别人聊个人生活中的矛盾处境,就有人问:人们应该如何去应对这种让人无力的境况?我当然知道,我无论提出哪种具体的建议,都会被觉得是一种不具有普世性的,甚至是一种“何不食肉糜”的解决方案。但我可能会建议先不去想那些宏大的社会结构,而是通过一些小事让自己得到充实感。应对社会结构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并不是说一定要立即消灭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要以一己之力改变世界,而也可以回到自己的生活领域,严肃地完成一些自己认为应当并且力所能及的事情,无论是劳作还是读书写作。这可能确实改变不了更多的社会关系,偶然的机遇因素造成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但我们可以在此之外去力所能及地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些想法用早年马克思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对象化劳动,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以自己为尺度,自由自觉地改造外部世界,将无机物变为自己的产品。凝聚了自己的劳动的产品,是我本质的外在化。通过这些劳动产品,我自己也能够获得一种所谓本质的实现——或者不用“本质”这样玄虚的词语——获得一种生活中踏实的感觉。社会关系中的难题很可能难以避免,但在社会关系之外还有个人生活领域,可以稍微获得一些在自己掌控范围内的弥补。可能是权宜之计,但也许是一个方法。
Q:感觉学长的叙述特别体系化。
A:有些事情我讲的很流畅,不是因为我思维敏捷,而是因为之前也和别人有过类似的谈话。生活中的问题往往也可以用学术语言表达,成为思考学业问题的材料,并形成自己的见解。虽然我的见解肯定不具有普适性,但能够让现在还没有遇到过重大挫折的我对过去和未来有比较明确的态度,能继续往前走。
马克思引用过一句话,“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句话原本说的是资本增殖的关键在于买入商品后需要再卖出换回更多货币,实现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跃。但把这句话做一个更广义的理解,大概可以说生活中也有或长或短或远或近的关键一步,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实现自己预期的行动,但至少要正视前面有考验,需要前进需要跳跃,并且坦然地意识到这就是我的生活,这是我不能逃避的事情,就在这里起跳,就在这里直面并投身于不确定的未来。
后补:马克思在另一处引用这句话时,他说道:“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Hic Rhodus, hic 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
(本采访完成于2022年10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