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悲剧之诗——读《新与旧》
居田 元培学院14级中文方向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只是战兵杨金标时隔三十六年的两次“例行公事”。曾在日头下跑马的青年战兵被时间磨成衰老的守门人——这最后一个刽子手终于死在古旧的城隍庙,血痕斑驳的鬼头刀却随着新的杀戮进入新的历史。
开篇“日头黄浓浓晒满了小县城教场坪”。坪里舞刀弄枪的影子,纵辔奔驰的影子,穿着各色号衣,来去如风。“光绪......年”的苍黄底色上,满地古艳神秘的影子乱人眼睛,摄人心神——“这神秘背后隐藏了动人的悲剧,同时也隐藏了动人的诗。”[1]
沈从文将这个本来或许并不动人的悲剧写成了动人的诗。
“相打到十分热闹时,忽然一个穿红号褂子传令兵赶来,站在滴水檐前传话:
‘杨金标,杨金标,衙门里有公事,午时三刻过西门外听候使唤!’”
十分热闹时来了这一件公事。晌午的敞亮浓到极致便成午夜的漆黑。午时三刻正好杀头。三个小猪仔炮似乎遥遥呼应了麦克白城堡的夜半钟声:
“得到许可,走近罪犯身后,稍稍估量,手拐子向犯人后颈窝一擦,发出个木然的钝声,那汉子头便落地了。”
此时静极。一擦,一落。后面是一片屏住呼吸的眼睛。一个头颅的血腥气味在明晃晃的大坪中间炸出一个黑糊糊的震惊。于是——
“军民人等齐声喝彩:(对于这独传拐子刀法喝彩!)”
一阵迟到的雷响。暴雨霎时淋透沉闷日头下的众人,辛苦冗长的生活在这里开一个缺口倾泻而下。只除了杨金标,狂欢的雨不向他头上倒。“木然的钝声”,罪的鬼影在他心上敲出空空,他还慌着——
“这战兵还有事作,不顾一切,低下头直向城隍庙跑去。”
青天白日的城隍庙里还有一出戏等他演回他自己。冰凉的四方地砖冷却热血溅过的凶刀,仪式性的四十红棍将他打回体魄健康自在快活的光身汉子。他被许可他杀头的力量摆在他的小小位置上,享受三钱二分银子酒肉,于是刀法棍责可以取乐。
“战兵年纪正二十四岁,还是个光身汉子,体魄健康,生活自由自在,手面子又好,一切来得干得,对于未来的日子,便怀了种种光荣的幻想。‘万丈高楼从地起’,同队人也觉得这家伙将来不可小觑。”
光荣的幻想直照未起的万丈高楼,万丈悲剧的影子便蒙住他了。杨金标是得了许可去杀应杀的人,为什么应杀,却是他虑不到的事情。杀头的技艺同人在马上显本事一样,都可观赏,都可评点。无非看本领如何,博取彩声和嘲笑。杨金标末了白日见鬼,或许因为他随身自带着一个鬼——刽子手的身份如影随形。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杀人被纳入一场事先安排好的理所应当的仪式。童年看杀头的经历和行伍经验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留下许多关于杀头的印记。与鲁迅不同,他有意无意地避让国民性批判的结论,而更关心如何多角度地返回杀头这件事情本身。如1929年他在《我的教育》中写到,剿匪“清乡”的背景下,“不杀人自然不成事体”,杀头也刺激着士兵单调的生活。
然而在天地间一个生命无故取消另一个生命,本身是极不自然的,这种人与生命的紧张情绪并不能被仪式合理化而消除,它只是在人造的严肃有序中暂时压制了。沈从文谈到凤凰军校阶级统治的弱点:“知道管理群众,不大知道教育群众。知道管理群众,因此在统治下社会秩序尚无问题。不大知道教育群众,因此一切进步的理想都难实现。”[2]一颗颗头颅在鬼头刀上涂抹刮磨不去的血痕,也在杨金标心里把阴影涂得越来越浓,最终成了致命的“习惯的力量”。
“习惯的力量”换个说法也就是“规矩”,是一种官神合作的约定俗成,它是新与旧中贯穿的恒定不变。老战兵的悲剧似乎是因为规矩的失落。然而“新”并不是没有规矩,它只是不守“旧”。又实际上,新规矩旧规矩内在逻辑一致,都要使不合道理的生活在种种严格的限制中看似合理地维持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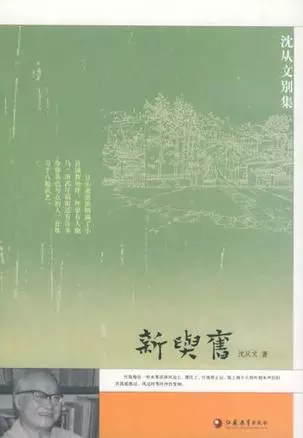
《新与旧》
《夫妇》里的捉、打,《月下小景》中的“不能结婚”,《巧秀与冬生》中的沉潭......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处处是奇特,诡异一至残忍的规矩。它们是湘西“老实、忠厚、纯朴、戆直的原人性情”[3]底下埋藏的阴影,是这阴影在社会习俗层面上的投射。恒常毒辣的日头下面,是这些影子把人根植在土地上。
人不长翅膀。长翅膀的是鸟和梦。梦之落空而近乎疯。疯近乎神。神是浪漫情绪与宗教专诚纠缠的结果。浪漫情绪亲近天空。而宗教专诚亲近泥土。边地求生的辛苦使苗民不得不用宗教规矩安排无告无望平凡日子。于是天神牵扯着天地,给湘西人撑开一种惯性的活法。
然而浪漫情绪长久压抑心底,往往变态:如沈从文所讲,在女子处表现为放蛊、行巫、落洞;在男子处呈现为游侠精神,极端而显现出蛮力和残忍。这种变态在战兵身上,则变现为从杀头得一些刺激与谈资。生与死的关系在种种矛盾中极端紧张。奇特的是原始的湘西有一股顽固蛮横的力量,平静地将这些变态的阴影都纳入日常。
边地的种族压迫中,苗人汉人都担负起一种悲惨的宿命:始终是神性魔性的矛盾,是灵魂向上升腾与堕落沉沦的撕扯。杀头的罪恶带着奖赏,看杀头的兴奋满足随着虚空凄凉。在穷苦又寂寞的现实里,纯粹的善与彻底的恶都不能实现,于是人人带了点隐性的疯狂,把平常日子按照分定过下去了。
最大的悲剧或许正是人对时间的无法可想。历史总还要给压抑忍耐着的渺小人类一点出其不意的打击:似乎与时间毫无关系的战兵,终于在改朝换代中把他不可小觑的光荣前景完全失掉。他作为最优秀刽子手的过去,被历史轻轻地撂在身后,那个“新”时代却还要一步一步从他脊骨上踩过去,把他踩成影子。
“新”终于是新的“旧”。“新的日月”并没有缓和历史和人性的紧张。杀人头颅的,仍是旧的野蛮。造成老战兵之死的,并不是新的愚暗。
老战兵不愿意同失去的旧规矩一道沉沦,也不愿意妥协于一群新鬼,但他无地可彷徨,在新旧的夹缝中作梦游一般的生活,听着“进去打死这疯子,赶快赶快”的喊声。
“你们做得好,做得好,把我当疯子!你们就是一群鬼。还有什么鬼?我问你!”他用性命讽刺了群鬼,自己沉没在黑暗里了。皱缩成一个老疯子的样貌,没有位置,没有尊严。这里并没有黄金世界,并没有无阴影的大光明。

沈从文
只要有新和旧的分别就会有新旧之际的梦魇。沈从文却不是自语或梦呓,他要讲故事给人听的。出于对湘西严肃质朴的同情,出于对命运与生活不合理分配的愤愤,他想做点什么来改善湘西的历史处境,为辛苦挣扎的湘西人在时代巨变中找到可以安居的位置。
他用十分克制的笔法,一脉脉梳理过去,把激动和不平忍在文字深处。在这里,作者不露声色地化身老战兵的自言自语,化身为一切背后无边无际的时间。种种变动发生在一条长河之上,而长河却终日不息地流淌下去。这一切都收在老战兵寂寞的眼睛里,却照出了作者对历史的态度:历史是一条河,常与变、新与旧,不过是悲剧惯性的重演。
沈从文不是通过写作完成对湘西的俯视与审判。他在写作中自省,对湘西苗民命运的思索同时也是摸索自己的来路。如他在《凤凰》一篇中写道:“若不能在调查和同情以外有一个办法,这种人总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地狱俨然就是为他们而设的。他们的生活,正说明‘生命’在无知与穷困包围中必然的种种。读书人面对这种人生时,不配说同情,实应当自愧。正因为这些人生命的庄严,读书人是毫不明白的”。
“有来路,才有自我。”[4]“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5]对苗乡新与旧的反思中,集“乡下人”与“读书人”双重身份于一身的沈从文,为湘西也为自己在变动的时代中求一合理的安放。
新与旧本来只是时间的流转,真正造成悲剧的,是旧习惯的蒙昧虚伪,是新规矩的蛮横无情。这是沈从文作品中一贯的态度:他倾心忠厚戆直的原人性情,认真庄严的活法;警惕“新的普通教育,造成一种无个性无特性带点世故与诈气的庸碌人生观”[6]。用鲁迅的话讲就是“伪士当去,迷信可存”。
而写作是对湘西的一个遥望,距离成就了“动人的悲剧”和“动人的诗”。对无尽的时空,菲利普·拉金在《这就是诗》里冷冷地说出:“人类彼此传递不幸,像大陆架层层加深。”[7]这是沈从文说不出的话。沈从文不这样说,或许他不忍心如此思考人的运命。
尽管小说中前景并不乐观,新的生命并不能因其“新”而摆脱蒙昧的阴影:“小学生好象很欢喜他们的先生”,喜欢学生的老师要掉脑袋,小学生一齐抬起头来笑着。脑袋掉了就掉了,喜欢忘了就忘了。日子会过下去,新人老成旧人,旧人又被新的日常带走。
可是沈从文深知,“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8],但他总怀着一个理想主义的愿望,要“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凝固下来。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9]他珍惜人的生命,因为生命有美,生命能美。人类通过生命的流注,在荒诞的时空中寻找存在的意义。对永恒的艺术而言,无所谓“新与旧”。
如果变化、矛盾与毁灭无可挽回,写作者对世界,究竟能做什么?沈从文给出的答案或许是爱抚。如黄永玉所说,“谁能怀疑他的文字不是爱抚出来的呢?”沈从文内心土地般广大深厚的温情为残酷的悲剧作了依托,坟头的庄稼依旧结实,一茬茬生命还要在这地里迎来送往。而沈从文有限的生命果真在动人的悲剧之诗中延长扩大,常读常新。
[1]《凤凰》(沈从文散文集《湘西》)
[2]《凤凰》(沈从文散文集《湘西》)
[3]《常德的船》(散文集《湘西》)
[4]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
[5]《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别集》)
[6]《沅水上游的几个县份》(散文集《湘西》)
[7]冷霜译。原句:
“Man hands on misery to man.
It deepens like a coastal shelf.”
[8]《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别集》)
[9]《抽象的抒情》(《沈从文别集》